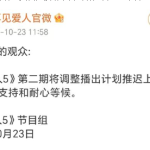继西藏 “烟花炸山” 事件引发生态质疑并导致多人被免职后,艺术家蔡国强团队于 10 月 22 日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再启烟花表演。这场为纪念场馆闭馆翻新的《最后的狂欢》,将建筑外墙化作 “巨型画布” 的白天烟火秀,却因现场弥漫的浓烟被部分观者形容为 “宛如战场”,再度将这位以火药为媒介的艺术家推向舆论中心。
此次争议并非孤例。此前 9 月,蔡国强团队在青藏高原的烟花活动已遭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公开反对,协会指出强光与噪音可能导致鼠兔洞穴坍塌、干扰动物繁殖,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影响。而蓬皮杜的表演虽选址城市艺术地标,却重蹈 “视觉争议” 覆辙 —— 白天燃放的烟火产生大量弥散性烟雾,与蓬皮杜标志性的钢管建筑交织,形成 “乌烟瘴气” 的视觉冲击,与 2014 年上海《九级浪》表演引发市民报警的场景颇为相似。
但在争议背后,是艺术家一贯的创作逻辑。蔡国强将此次表演定义为 “最后的狂欢”,延续了其对 “毁灭与创造” 主题的探索,这与 2020 年《悲剧的诞生》中致敬 “不屈与希望” 的内核一脉相承。表演中黑白交替的烟火 “狂草”,既呼应张旭、怀素的书法精神,也暗藏毕加索《酒神节》的狂欢意象,延续了他融合东西方文化符号的创作路径。其团队强调使用 “无毒、环保、CE 认证” 的烟花产品,试图回应外界对污染的担忧。
舆论场的分裂实则指向艺术评价的核心矛盾。支持者援引艺术史学者西蒙・沙马的观点,认为 “伟大艺术是艺术家与媒介的艰难谈判”,烟火的不可预测性正是其魅力所在;反对者则延续对 “烟花炸山” 的批评逻辑,质疑其 “以艺术之名制造惊扰”,忽视公共空间的接受度。这种分歧在巴黎与上海的待遇差异中早已显现:同样的烟火表演,在巴黎被赞为 “文化盛事”,在上海却因预警不足沦为 “社会新闻”。
从《天梯》的宇宙叙事到如今的场馆告别,蔡国强始终以火药为笔挑战艺术边界。但 “烟花炸山” 的教训与蓬皮杜的争议共同警示:当艺术走出专属场馆,其自由表达需与公共利益达成平衡。这场 “最后的狂欢” 或许正如他所言,是 “认清痛苦仍要享受生命” 的隐喻,但如何让烟火的光芒而非烟尘留在公众记忆中,仍是这位 “火药艺术家” 需要解答的命题。